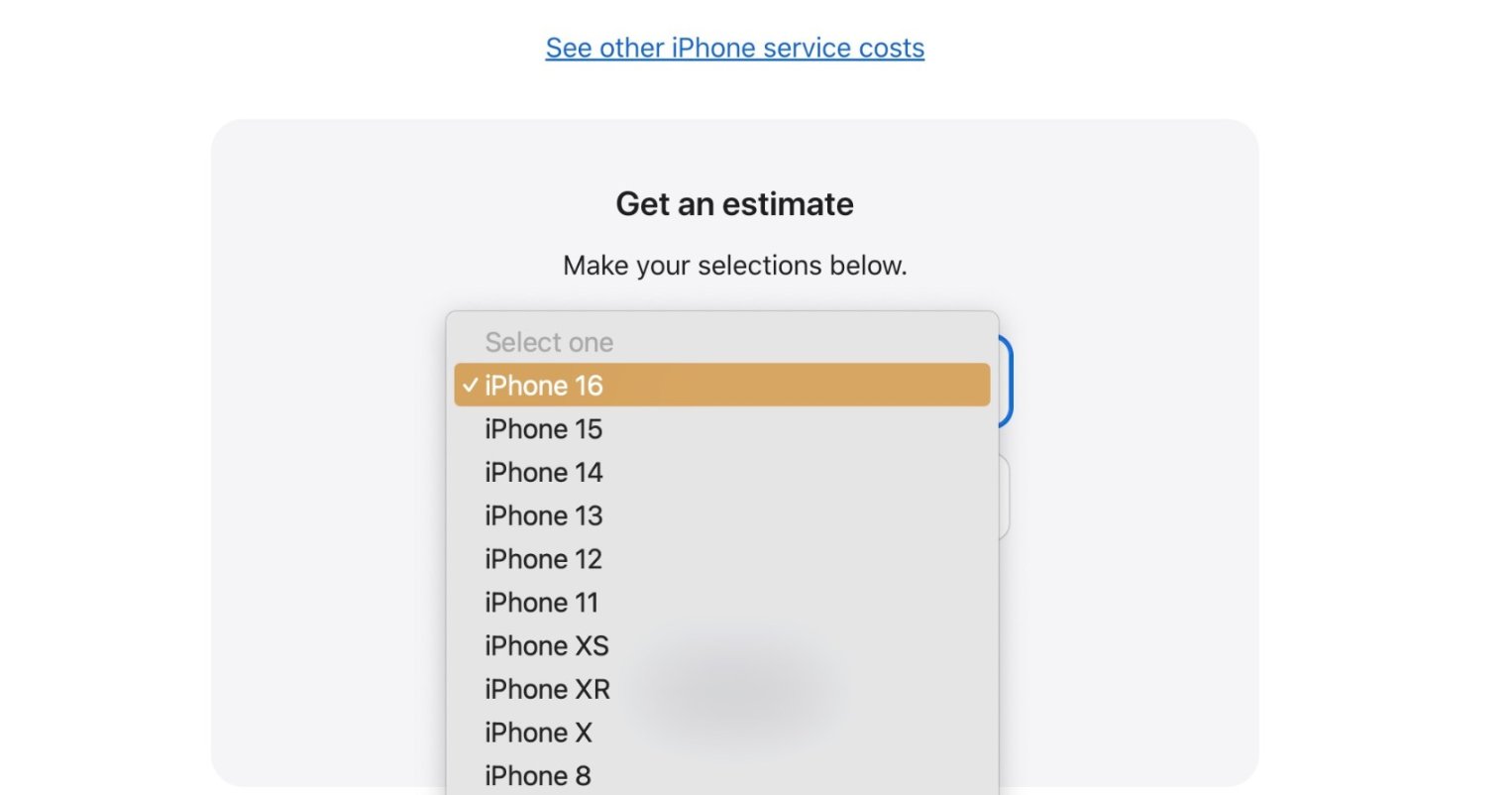今天有幾個觀察,趁熱記下來。
和朋友聊起他們一家被投公司的組織問題。公司業務發展得還行,但創始人的管理風格一直是個坎——高管來了又走,組織能力始終搭不起來。他們嘗試過各種方式:私下溝通、引入顧問、做組織診斷報告。效果有限。這周他說準備把這事拿到董事會上彙報。我當時心想,這不是把私下的事公開化了嗎?後來想明白了——這是在用「儀式感」製造行為約束。Cialdini講過「承諾與一致性」原則:人一旦在公開場合做出承諾,就會產生強烈的內驅力去保持一致。董事會這個場合,讓創始人公開表態支援變革,比私下說一百遍都有效。「話說出去了,就不好意思不幹了」
另一個關於「二代」的觀察。行業裡經常給「二代」貼標籤——不夠拼、吃老本、守成者。這周碰到一個例子讓我重新想這個問題。某上市公司的接班人,接手十年,業績翻了十倍。現在四十歲不到,對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非常清楚。這哪裏是守成者,分明是創業者的profile。想起中國歷史上的廟號體系:「祖」是開創,「宗」是守成。康熙明明是第四代皇帝,廟號卻是「聖祖」而非「X宗」——因為他的功業是開創性的,不是守成。評價一個人是守成還是開創,看的不是他是第幾代,而是他任期內做了什麼。傳統框架可能需要修正:看的不是標籤,而是任期業績增長倍數、有沒有清晰的能力邊界認知
聽說一個跨境併購的扎心案例。朋友在看一個歐洲工業標的,各方面都不錯,但被PE賣方關在門外。原因很簡單:他們被自動貼上了「戰略投資者」標籤。對方的推斷鏈條是:戰略買家會搞運營整合、會裁員重組、而且背景敏感觸發監管審查。Spence的訊號理論在這裏演繹得很清楚——標籤本身就是訊號,會觸發一系列推斷。更麻煩的是,想洗掉這個標籤幾乎不可能,因為機構身份是公開的。這件事的啟示可能是:在敏感交易中,訊號管理需要前置到專案篩選階段,而不是等到被關門才反應
同一個標的還有個有意思的細節。賣的是一個重大少數股權,不需要控股方的同意就能轉讓。一開始我覺得少數股權不夠有吸引力——畢竟不能完全控制公司。後來想明白了:少數股東有時候有「超比例影響力」。控股方需要維護和新股東的合作關係,尤其是在日常運營、重大決策方面都需要配合。你佔25%或40%,但你在董事會有席位,有否決權事項,有資訊權。權力不一定來自你能做什麼,有時候來自你可以選擇不做什麼——不配合、不投票、不簽字。這是一種「負面槓桿」
某個併購專案學到一個節奏控制的lesson。團隊對標的很感興趣,想追加一次會面。我說不行。Schelling講過,在談判中「顯示自己有退出選項比顯示自己需要這筆交易更重要」。你約了一次會還要追加,就等於傳送「我非常需要這個deal」的訊號。賣方會據此更新對你保留價格的預期,然後提高要價。保持從容的外部形象,本質上是在管理對方對你底牌的推斷
還有一個關於交易中介的觀察。某個標的是透過一個「萬能中間人」接觸到的,他對買賣雙方的情況都很瞭解。問題在於,他的目標是最大化自身參與度——變成FA賺錢、自己也投一點、甚至想當管理層,一條龍全包。而買方的目標是以最低成本完成交易。激勵完全不相容。更麻煩的是,一旦他知道你在推進,他就會想辦法深度參與,因為他擁有對雙方的資訊優勢。「請神容易送神難」。正確策略可能是解耦:先透過其他途徑建立渠道,途徑走通了再決定找誰來操盤
AI工具這邊有個有意思的現象。一個朋友開發了一套會議問答的workflow:老闆連問五個問題,以前你得五個都會,現在只要會第一個——AI在你回答第一個的時間裏就把後面四個處理完了。用程式設計的話說,這是把時間複雜度從O(n)降到了接近O(1)。學過演算法的人知道,把排序從O(n²)最佳化到O(n log n)就已經很厲害了。現在AI在某些場景下實現的,是把人的「認知負載複雜度」從線性降到常數級。提問的價值不再是「測試你知不知道」,而是「測試你的判斷力和工具使用能力」
與此相關的另一個觀察:Context積累比知識本身更有價值。朋友的做法是「所有活都在AI環境裡幹」,所以他可以問AI「上週我在幹啥」。記憶是工作的副產品,不需要額外的記錄行為。這改變了知識管理的邏輯:以前是主動儲存、被動檢索;現在是被動積累、主動呼叫。未來的生產力工具競爭,可能是「Context積累深度」的競爭——使用者不是爲了功能留下,而是爲了已經積累的context留下
投資主題那邊有個時間敏感的視窗。某個細分賽道形成了雙寡頭格局,兩家加起來市佔率超過70%。關鍵訊號是政府資本入場了。Peter Thiel講過,政府不是好的創新投資者,但卻是優秀的「規模化推廣」投資者。政府資本入場本身就是一個訊號:政策制定者認為技術已經成熟,值得用公共資源推動產業化。歷史經驗看,政府資本入場後的12-24個月往往是最佳投資視窗——政策紅利開始釋放、競爭格局尚未固化、但退出路徑已基本清晰
最後一個觀察,關於「支援朋友」這件事。這週一個朋友遇到職場困境,在她的體系裡是個大事。我本能地想用自己的框架去「開導」她——覺得那個體系的評價不重要。說完之後覺得哪裏不對。後來反思,發現問題:False Consensus Effect——假設她應該像我一樣不在乎;Dismissive Response——用「這又如何」來否定她的焦慮;Value Imposition——用自己的價值觀去否定她的處境。核心問題是:我的「支援」更多是在表達自己的價值觀,而非幫她解決她定義的問題。即使不認同某個系統,也應該尊重朋友在那個系統內的選擇和約束
今天就這些。不成體系,但寫下來可能以後有用。很多判斷現在也不知道對不對,過半年回看再驗證